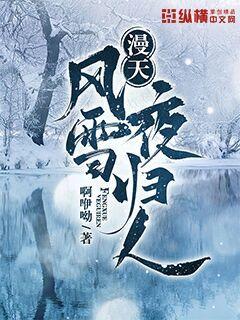梅夏一睁眼,发现自己身在一座爬满了葡萄藤蔓的凉亭里,亭子样式古朴,正中间放着一方大理石圆桌,桌旁落着四个圆柱形的石凳,他刚才似乎竟是趴在这石桌上睡着了。旁边有个婢女正在斟茶,看他醒来,迷迷糊糊地四处张望,抿着嘴,掩帕而笑。
梅夏站起身来,朝凉亭四周望去,一片雾霭而已,细细看去,方有无数奇峰异海的轮廓收入眼底,远处一群白鹤鼓翼长鸣栩栩然而来,收回目光,看向凉亭里的葡萄藤,上面尚坠着一串串青涩果子。
“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他疑惑发问。
那巧笑倩兮的婢女,笑着应道,“怪不得小姐经常说公子是个痴人,常说一些没头没脑的痴话。公子忘了,公子本是君上亲命的司掌下界采诗的诗律郎,昨晚您在这里和近日从下界飞升上来的青莲居士喝酒论诗,想是喝醉了,就在这里睡了一整宿。”
“那你家小姐又是谁?”
那侍女又答,“我家小姐,自然是那司百花花时的百花之主,是您最好的朋友。”
那“朋友”二字咬得格外软糯,“我们问过我们小姐,小姐只说,采诗的自然要采花呀!”那侍女一脸促狭笑意瞅着梅夏,“只是想问公子这采花是怎样采法?”
梅夏觉得自己没听懂,但脸仍然不争气地红了,呼呼地吹着气。
“我去下界采诗?怎么采啊?”梅夏一脸无知且无辜的表情,仿佛那和他自己本人一点关系也无。
那小侍女瞪大眼睛,可爱地问道,“公子连这都忘了,我得告诉小姐去,说公子醉了一觉,好像傻了。”
不过她并没有离开,而是双手托着脸颊,耐心地,一边回忆一边说,“当今君上酷爱诗歌,因此经常命人将一些大道气运用一些绝妙诗词做装饰,洒向人间,那些凡间运气比较好的修道之人,偶尔领悟到了一些,便可以此获得天上的眷顾,修道顺利,听说下界有‘儒八道九释十三’之说,但无论是哪一种,修炼到一定程度,都要凝成‘心符’这样一种东西,才算真正踏进大道的门槛里。”
“心符?这个我好像听说过!”梅夏眼睛一亮,像学塾里乖乖听讲的小学生。
“那些心符其实并非是一样事物,例如花草树木,虫鱼鸟兽,而是关于一个或一些事物的一首诗歌,这些诗歌是固定的,每个人的心符如果能领悟到最圆满的境界,也就是能够完全领悟到关于那种事物的那首诗歌所表达的意境,就能得到最多的大道气运,修行的上限也就越高。譬如桃花,有些人领悟到的是‘竹外桃花三两枝’,只是当成寻常美景,有些人领悟到的是‘人面桃花相映红’,这便极为接近了,据说最为接近圆满的‘桃花心符’,是那句‘逃之夭夭,灼灼其华’,讲的是身着红色嫁衣的女子立于桃花之下的意境。这您难道也忘了?”
“确实忘了。”梅夏不好意思地笑着。
“哎,看来是病的不轻了。关于每样事物的‘心符’所对应诗歌,还都是您来勘定的呢,当然那句‘桃花’有关的,也是您亲自选定的。您是君上亲封的诗律郎,这就是您的职责啊。”
梅夏这下吃惊不小,自己啥时候这么厉害了?
“不过凡物必是有始有终,有成有败,花开便有花落,所以每种心符最圆满境界由一首诗规定,其摧灭也由一首诗来规定,不过因为这牵涉他人性命,所以很少有人知晓。”
梅夏若有所思,偶然抬头,却见一片桃花与李花飞散,红白相间,纷纷扬扬地不知飘向哪里,不知为何,却已泪流满面。
在哥哥梅清背上睡了一整夜的梅夏,一觉醒来,揉了揉眼睛,发现到了一座山中的建筑前,上写着“梦觉寺”三个大字。
关于梦觉寺,其实别有一段故事。
梦觉寺被称作寺,结果主人却是一个书生和道士,这虽然令人疑惑,却实在是不得已的妥协的产物。寺中不设佛像,不收香火,不接俗客,甚至附近的人都知之甚少,实在是因为寺中人本就很少,又几乎不怎么与外界接触,仿佛是个神秘的世外桃源。当初鲁山海和玄微子相识,一见如故,对对方才学修为十分钦佩,遂约定找一处安定之所互相切磋质诘,两人见闻经历所修功法截然不同,一南一北,一儒一道,但不同恰恰意味着可以互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互辩难,对自己的修为进境也很有帮助。两人皆是一眼便看中此处,玄微子自然是因为此处迥出人境,灵秀蔚然,山环水绕,旁边两峰排闼,青松翠柏入眼而来。更重要的是突然看到一只白色的蝴蝶飘摇直上九霄,心中大喜。鲁山海则是因为山腰盛开的一簇簇桃花,桃花照影溪中,映得满川尽是浓艳鲜红之色,令他有些怀念昔日在邓林峰的种种,不由得神思一片恍惚。于是两人毫不犹豫选择在此处开辟居所,但却因为名字意见分歧。鲁山海认为应该叫做桃花阁,玄微子主张叫作蝶梦居。按理说,名者实之宾也,你一个道士,你祖师爷庄周都这样说了,你干嘛还这么在意这点命名的事情,鲁山海当时就这么驳斥玄微子,玄微子却只是点头微笑,保留意见,气的鲁山海差点要跳起来。最后二人都没法说服对方,最终只能找一个双方都不反对的名字,不称阁,不称居,偏称寺,也是有戏谑之意,二人虽于各自所学的功法知之甚详,却于流传于华夏大地之上关于西方佛国的吉光片羽一知半解,所以这戏谑之意之外也包含着二人求学问道时刻不忘有他山之石的想法。最后定名为梦觉寺,则是因为那句“大梦谁先醒,平生我自知”,人生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现实可如梦境恍惚,梦境中谁又能说没有半分真实?
一声似近似远的鸡啼响彻整个清源小镇,东边的天空升起灿烂的朝霞,按照“朝霞不出门”的谚语来看,最近两天应该是要下场雨了。也是时候下场及时雨了,田里的庄稼需要,春天里破土而出的西瓜现在已经长出了不短不长的瓜秧,也需要一场雨水的滋润。
几乎一夜未眠的妇人,仍然按时起床做饭,像往常一样,听完两个孩子各自背了两篇《诗经》篇目,才开始一起吃饭。小男孩低着头飞快地往嘴里扒饭,略微懂事的丹青见父亲的身影并未出现,就问“父亲不在家?”男孩这才注意到,也望向母亲,妇人只是平静地说,“没事,你爹出门有事了。赶快吃饭,吃完饭送你们一起去学塾。”
锦衣玉食的生活虽然安逸,但她并不后悔放弃这一切,跟着那个不太爱说话的男子来到江南,一日三餐家务是平淡生活的趣味,地里种豆种瓜是书院闺阁里难以接触到的田园之乐,更重要的是,有爱人相伴,儿女相随。十来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对于历史沧桑传承千年的大族而言自不算长,却已足够让她忘记自己前面二十年的小姐生涯,尽管那是儒门中赫赫有名的卜家,和端木家并列为传承《诗经》的两大家族的卜家。
“我吃饱了!”男孩把碗筷往桌上一丢。“我不要木剑了,我将来要当一个读书人!”
听了弟弟的豪言壮语,丹青笑着说,“你昨天还说要当一个行走江湖的剑客呢!”
“我改主意了!读书人没那么危险,这样母亲就不会担心我了。”
丹青有些诧异弟弟突然变得这么懂事,母亲却差点掉下眼泪,但还是坚强地忍住了,忙说,“读书人好啊!将来春联都不用买人家的了!”
“青儿,你学塾里的先生姓什么?”因为记得昨日丈夫提了两句,说这位先生当是北方诗礼传家的大族出身,她还未来得及询问。
“好像是姓端木,我们都叫他端木先生。”
“端木先生”,妇人口中喃喃地重复着,似乎因为要压制心中的悲伤而对眼前的一切有些麻木,丧失了往日的清醒和机敏。又念叨了两句,才回过神来,“端木先生?”
卜家和端木家是北方儒门中共同传承《诗经》千年的大族,后人著书中有一句“子夏传炫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说的便是此事。不过虽说两家先祖千年之前皆位列圣人门下十大贤人,并且都以《诗经》传家,但还是有些微差别,比如卜家先祖文学才能出众,后世世代文人学士辈出,而端木家则亦精通商贾之术,以及比较烧钱的医家学问。两家平日交流沟通不少,相互之间也有些许了解。
“端木先生长什么样子?”
女儿嘴里还嚼着米饭,咕咕哝哝地说,“你今天不是也一起去学塾吗?”到时自然就会见到。“不过端木先生好像是很厉害的郎中,经常有人来求他治病的!”
妇人恍然大悟,那人很可能就是端木家的三公子了!想着待会可能会见到年轻时的相熟之人,妇人便油然生出近乡情怯之感。只不过这一点怯乡的心思很快就被对丈夫的担忧和不幸的猜测冲散。往常也断断续续听丈夫讲过一些他以前的事,不过他的过往几乎所有事都已经放下,在和她相遇,生儿育女,组建家庭之后,往事已经如烟霭消散,唯独一件事或者一个人他一直没有放下,毕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他而言,师恩重于泰山。而且昨天听丈夫的意思,便是为那件事而去。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带着孩子,在家里等着他平安归来。